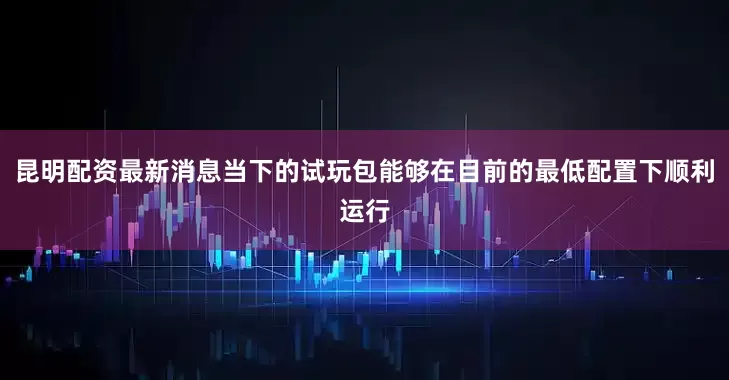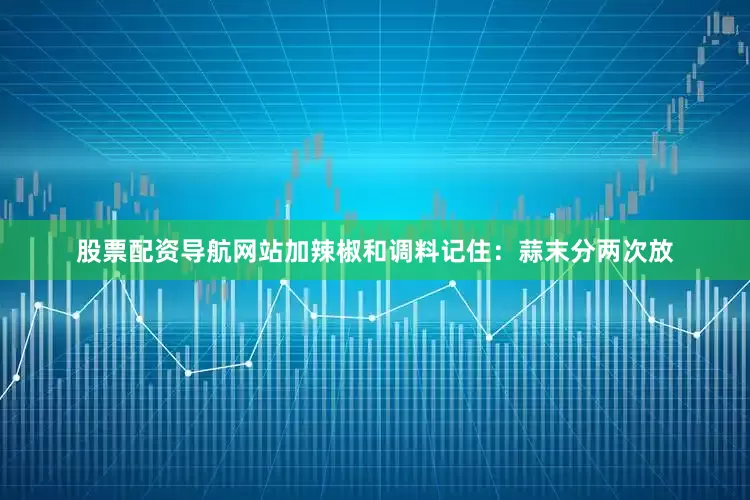01
1941年7月22日深夜11点37分,建阳镇。
雨水顺着屋檐哗哗流下,在青石板路面上激起一片水花。新四军第3师第7旅19团政委王东保裹紧军装,在泥泞的街道上巡视着。这是他第三次查哨了——作为一名政工干部,他有种说不出的不安感。
建阳镇的夜晚静得可怕。这个位于射阳河畔的小镇,往常即便在深夜也会有些狗吠声,但今夜,除了雨声,什么都听不见。王东保停下脚步,仔细倾听着。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驳壳枪,那是他从一个日军军官手里缴获的,枪柄上还刻着日文。
就在此时,前方巷口突然闪出两个黑影。
借着微弱的月光,王东保看清了——是两个日本兵!他们正押着两名新四军女兵往巷子深处走。女兵中有一个他认识,是军部医疗队的小李,江苏无锡人,才19岁。
“有敌人——”小李的尖叫声撕破夜空。
日本兵慌忙捂住她的嘴,但为时已晚。王东保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,驳壳枪在手中快速转动。作为一个曾经在红军时期就以枪法精准著称的老兵,他的动作行云流水。
“砰!砰!”
两声枪响在雨夜中格外清脆。两个日本兵应声倒地,鲜血在雨水中迅速晕开,染红了青石板。
王东保来不及检查敌人是否毙命,一把拉起两个女兵:“快走!日本人摸进城了!”
话音未落,建阳镇外围突然枪声大作。密集的机枪声夹杂着三八大盖的射击声,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。王东保心中一沉——这不是小股部队的偷袭,这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进攻!
02
12个小时前,下午2点。
彭明治骑在马上,望着前方的建阳镇,眉头紧锁。这位36岁的旅长,脸上写满了疲惫。从7月20日开始,他们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好好休息了。
“旅长,部队实在走不动了。”参谋长李明走过来,声音有些沙哑,“战士们两天没吃热饭了,再这样下去,别说打仗,连路都走不动。”
彭明治点点头。他知道部队的状况——从盐城突围出来,一路且战且走,战士们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。更要命的是,他们还要掩护军部机关,那里有新四军的核心领导层,包括代军长陈毅、政委刘少奇,还有大量的机要文件和电台设备。
“传令下去,一营进城休整,二营、三营在镇外设防。”彭明治下达命令,“记住,只休息4个小时,天黑前必须继续前进。”
建阳镇的街道异常冷清。这让彭明治心中升起一丝不安。按理说,即便是战争时期,镇上总该有些百姓活动的痕迹。但现在,家家户户门窗紧闭,连条狗都看不见。
“旅长,您看。”警卫员小张指着路边的一家米店。
彭明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只见米店的门虚掩着,门框上有新鲜的血迹,地上散落着几个日式饭盒。很明显,日军最近来过这里。
“加强警戒。”彭明治压低声音,“告诉各连,埋锅造饭要快,吃完立即准备战斗。”
雨在傍晚时分开始下起来。先是毛毛细雨,很快就变成了瓢泼大雨。战士们顾不上避雨,抓紧时间生火做饭。两天没吃热饭的肚子已经在抗议了,有个战士甚至等不及饭熟,就开始啃生米。
彭明治站在临时指挥部里,面前摊开一张军用地图。这是从一个日军少佐那里缴获的,上面详细标注了苏北地区的地形和日军据点分布。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着,最后停在建阳镇西北方向的一个红点上。
“这里有个日军据点。”他对参谋长说,“直线距离不到8公里。”
“要不要派侦察兵去看看?”李明建议。
彭明治摇摇头:“来不及了。我们必须赶在天黑前离开。日军的‘扫荡’部队主力还在后面,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。”
然而,他不知道的是,就在建阳镇的某个角落里,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街道上的新四军战士。
03
那双眼睛属于王老三,建阳镇有名的地痞,也是日军的眼线。
王老三原本是个赌徒,去年输光了家产,老婆也跟人跑了。走投无路之际,驻扎在附近据点的日军中队长仁川次郎找到了他。仁川给了他50块大洋,让他在建阳镇当“情报员”。
看着街上的新四军战士,王老三心里盘算着。如果这个情报报上去,仁川肯定会重重有赏。想到这里,他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雨越下越大,王老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日军据点跑。8公里的路,他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跑到了。当他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据点门口时,哨兵差点开枪。
“太君!我有重要情报!”王老三用蹩脚的日语喊道。
很快,他被带到了仁川次郎面前。
仁川次郎,42岁,东京人,陆军士官学校第37期毕业生。他身材不高,但眼神锐利,留着标志性的仁丹胡子。作为一个在中国战场上打了4年仗的老兵,他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。
“多少人?”仁川用中文问道,他的中文说得很流利。
“看上去有一个营,三四百人。”王老三比划着,“都进了镇子,正在做饭呢。”
仁川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最近上级一直在催促他们加强“扫荡”力度,如果能消灭一支新四军部队,那可是大功一件。
但仁川没有立即行动。他了解新四军的战术——他们善于诱敌深入,然后来个反包围。自己手下只有150人,如果贸然出击,很可能中计。
“发电报给附近的各据点,”仁川对副官说,“就说发现新四军主力,请求支援。”
两个小时后,来自三个据点的援军陆续到达,加上仁川的中队,总兵力达到了500多人。这个兵力对付一个营的新四军,应该绰绰有余。
晚上10点,仁川召集各部军官开会。
“根据情报,新四军大约有一个营在建阳镇内休整。”他指着地图说,“我们分三路进攻。第一路,由山田少尉带领50人,从东门潜入,负责在镇内制造混乱。第二路,我亲自带领主力300人,从南门发起正面进攻。第三路,由松井少尉带领150人,在西门设伏,防止敌人突围。”
“中队长阁下,”山田少尉有些担心,“如果敌人不止一个营怎么办?”
仁川冷笑一声:“新四军刚从盐城突围,疲惫不堪,武器弹药也不足。就算有两个营,我们500精锐也足够了。记住,这次要速战速决,天亮前必须结束战斗。”
04
夜里11点30分,山田少尉带着50名日军,悄悄接近建阳镇东门。
雨还在下,这给他们的潜入提供了掩护。日军士兵都脱掉了皮鞋,赤脚走在泥地里,尽量不发出声音。他们分成十个小组,每组5人,像幽灵一样潜入镇内。
其中一组的目标是镇中心的新四军临时指挥部。根据王老三提供的情报,那里应该有新四军的指挥官。如果能够斩首成功,战斗就结束了。
然而,他们低估了新四军的警觉性。
新四军在长期的游击战中,养成了极其严密的警戒习惯。即便是在相对安全的镇子里休息,他们也设置了三道警戒线:明哨、暗哨、游动哨。
当山田的部下摸到第二道警戒线时,被暗哨发现了。那是一个19岁的新四军战士,湖南人,名叫张小山。他藏在一个屋檐下,本来都要打瞌睡了,突然看到几个黑影从雨中闪过。
张小山立即警觉起来。他没有立即开枪,而是悄悄跟了上去。当他确认那是日本兵后,立即吹响了报警的哨子。
尖锐的哨声在雨夜中响起,整个建阳镇瞬间活了过来。
“敌袭!敌袭!”
新四军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,抓起枪就往外冲。有的战士连鞋都没穿,赤脚踩在泥水里。

与此同时,镇外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仁川的主力部队发起了进攻,300多名日军端着刺刀,呐喊着冲向新四军的防线。
彭明治从床上一跃而起。作为一个老兵,他能从枪声的密度判断出敌人的规模。
“至少有300人,不,可能更多。”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对参谋长说,“命令19团守住南门,20团从西门突围,21团掩护军部先走!”
“是!”李明转身要走,突然又回过头,“旅长,我们怎么办?”
“我带预备队断后。”彭明治拿起毛瑟手枪,检查了一下弹匣,“记住,保护军部是第一要务。告诉陈代长,不要管我们,立即转移!”
李明眼眶有些发红:“旅长……”
“执行命令!”彭明治厉声道。
建阳镇南门,19团3营正在拼死抵抗。营长赵大海,山东汉子,虎背熊腰,手里端着一挺捷克式轻机枪,对着冲上来的日军猛烈扫射。
“同志们,顶住!为军部争取时间!”他大吼着。
子弹在雨中飞舞,不时有战士中弹倒下。日军的掷弹筒开始发威,一发发榴弹落在新四军的阵地上,炸起一片片泥土。
就在这时,王东保带着两个女兵跑了过来。
“营长,镇子里也有鬼子!”他气喘吁吁地说。
赵大海脸色一变:“多少人?”
“不清楚,但至少有几十个。他们在到处放火,制造混乱。”
这下麻烦了。赵大海意识到,日军这是要来个里应外合。如果让镇内的日军得手,整个防线都会崩溃。
“王政委,你带一个连去清理镇内的鬼子。”赵大海当机立断,“我在这里顶着!”
王东保点点头,带着一个连的战士冲回镇内。街道上已经乱成一团,到处是枪声和喊叫声。几处房屋着了火,火光映红了半边天。
05
军部驻地,陈毅正在紧急销毁文件。
“代长,快走吧!”警卫员焦急地催促。
陈毅摇摇头:“还有最后一份文件。”他手里拿着的,是新四军最新的部署图,绝对不能落入敌手。
火光中,这位40岁的新四军代理军长显得格外镇定。皖南事变后,他临危受命,重建新四军,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。现在,他必须再次带领部队突出重围。
“报告!”通讯员跑进来,“21团已经打开西门通道,请军部立即撤离!”
陈毅把最后一份文件扔进火里,站起身来:“通知各部,按原计划撤退。告诉彭明治,不要恋战,保存实力要紧。”
就在军部开始撤离时,彭明治正带着预备队在镇子中心阻击日军。他手下只有两个连,不到200人,却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。
“旅长,我们也撤吧!”警卫员小张喊道。
彭明治没有回答,他在倾听着什么。雨声中,除了激烈的枪声,他还听到了别的声音——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声,还有……迫击炮!
“不对劲。”彭明治自言自语。
“什么不对劲?”李明问道。
“日军的火力配置不对。”彭明治皱起眉头,“如果真有我们预计的那么多敌人,不应该只有这点火力。听这机枪声,最多四五挺,迫击炮也就两三门。”
李明也是老兵了,仔细一听,确实如此:“难道鬼子在虚张声势?”
彭明治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:“不是虚张声势,是兵力不足!他们最多只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!”
“那我们……”
“传我的命令,”彭明治果断地说,“停止撤退,全旅反击!”
这个命令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,不撤退也就罢了,还要反击?
“旅长,军部的安全……”李明提醒道。
“军部已经安全撤离了。”彭明治看了看表,“按照时间计算,他们已经走出5公里了。现在,该轮到我们了!”
06
仁川次郎正在指挥部里踌躇满志。
“中队长阁下,新四军开始撤退了!”传令兵报告。
仁川露出得意的笑容:“很好,命令各部追击,不要让一个新四军逃脱!”
然而,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,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。
原本正在撤退的新四军,突然停了下来,然后,如潮水般反扑回来!
“杀!”
震天的喊杀声响起,新四军战士端着刺刀冲了上来。他们刚才的撤退,只是为了重新集结兵力。现在,三个团近3000人,从三个方向同时发起反攻。
仁川的脸色变了。他这才意识到,自己中计了!建阳镇里不是一个营的新四军,而是一个旅!
“撤退!立即撤退!”他声嘶力竭地喊道。
但为时已晚。彭明治早就料到敌人会撤退,提前在各个路口设置了火力点。19团的十几挺机枪已经架好,就等着日军撤退时来个“关门打狗”。
日军的撤退变成了溃逃。在狭窄的街道上,他们成了活靶子。机枪子弹如雨点般扫过,日军士兵成片倒下。
仁川的战马被一发流弹击中,他被甩下马背,重重地摔在泥地里。当他挣扎着爬起来时,看到的是地狱般的景象——到处是尸体,活着的日军士兵四处逃窜,完全失去了建制。
“中队长,快走!”副官拉着他就跑。
他们跌跌撞撞地向西门逃去,那里是松井少尉的部队设伏的地方。如果能和松井会合,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
然而,当他们跑到西门时,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——松井的150人,已经被新四军20团包围了。
原来,彭明治在下达反击命令时,特意交代20团团长:“西门外肯定有日军埋伏,你带人绕过去,来个反包围。”
20团团长不负所托,带着部队从小路迂回,成功包围了松井的部队。现在,松井正在拼死突围,哪里还顾得上接应仁川?
07
凌晨2点,战斗进入尾声。
建阳镇已经完全被新四军控制,日军除了少数人逃脱外,大部分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。仁川次郎在混乱中被击毙,尸体被发现时,他手里还握着指挥刀。
彭明治站在镇中心,看着满地的日军尸体和缴获的武器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“清点战果。”他对参谋长说。
半小时后,统计结果出来了:击毙日军367人,俘虏58人,缴获步枪247支,轻重机枪24挺,掷弹筒8个,迫击炮4门,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。
而新四军的伤亡不到100人。
“旅长真是神机妙算!”李明由衷地赞叹,“您是怎么判断出敌人兵力不足的?”
彭明治笑了笑:“打了这么多年仗,听声音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。日军如果真有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兵力,火力密度不会这么稀疏。而且,你注意到了吗?他们的炮火一直很节省,这说明弹药有限,不敢放开了打。”
“那您为什么敢断定我们有兵力优势?”
“因为我了解日军的心理。”彭明治点了根缴获的日本烟,深吸一口,“他们以为建阳镇只有一个营的新四军,所以只调集了500人。如果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旅,肯定会调动更多兵力。这就是情报不准确的后果。”
这时,王东保走了过来:“旅长,在日军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物资,够我们用好一阵子了。”
“好!”彭明治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你今晚立了大功。要不是你及时发现潜入的敌人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王东保不好意思地笑了:“都是运气好。”
“这不是运气,是警惕性。”彭明治正色道,“在敌后作战,警惕性就是生命线。”
天快亮了,雨也停了。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抹鱼肚白。
彭明治下令部队立即打扫战场,准备转移。虽然打了个漂亮仗,但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——军部还在前方等着他们会合。
临走前,彭明治特意到镇外的日军据点看了看。这个据点修建得很坚固,有砖石结构的碉堡,还有完善的交通壕。如果不是日军主动出击,要攻下这个据点,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。
“有时候,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”彭明治自言自语,“但前提是,你得判断准确。”
08
三天后,新四军军部安全到达预定地点。
陈毅见到彭明治时,紧紧握住他的手:“听说你们在建阳打了个大胜仗?”
“侥幸侥幸。”彭明治谦虚地说。
“这可不是侥幸。”刘少奇走过来,“能在那种危急情况下,准确判断敌情,果断反击,这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判断力。”
陈毅点点头:“这一仗打得好,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,缴获了武器弹药,更重要的是,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,让日军知道,我们不是好惹的。”
“报告!”通讯员跑过来,“延安来电!”
陈毅接过电报,看完后脸上露出笑容:“毛主席来电祝贺,说建阳之战是游击战的典范,要求各部队学习7旅的战斗经验。”
彭明治激动得眼眶有些湿润。从红军时期开始,他就跟着毛主席打游击,深知游击战的精髓——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,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
这次建阳之战,表面上看是一次遭遇战,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游击战的灵活性。先是诱敌深入,让日军以为占了便宜;然后突然反击,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;最后围点打援,将敌人的预备队也消灭。
“彭旅长,”陈毅说,“你这次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,写个战斗详报,让其他部队学习。”
“是!”彭明治敬了个军礼。
几天后,建阳之战的详细战报传遍了新四军各部。这份战报不仅详细描述了战斗经过,还总结了几条重要经验:
第一,情报工作的重要性。虽然这次是敌人的情报出了问题,但也提醒我军,必须做好自己的情报工作,知己知彼,才能百战不殆。
第二,灵活机动的战术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,不能死守硬拼,要善于利用运动战消灭敌人。
第三,指挥员的判断力。战场情况瞬息万变,指挥员必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,做出正确的判断。
第四,部队的执行力。彭明治敢于下达反击命令,是因为他相信部队的战斗力。而部队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,在接到命令后,立即行动,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
然而,这份战报没有提到的是,这次胜利背后还有一个小插曲。
那个向日军通风报信的汉奸王老三,在日军溃败后,想要逃跑,被愤怒的镇民抓住了。镇民们要求处决这个汉奸,但彭明治制止了他们。
“让政府来处理他。”彭明治说,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,不能随意杀人。”
最后,王老三被送到根据地政府,经过审判,被判处了死刑。行刑前,他痛哭流涕,说自己对不起乡亲,对不起国家。
“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。”围观的群众中,有人这样说。
建阳之战后,日军的“扫荡”势头被遏制了。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新四军的战斗力,在此后的行动中变得更加谨慎。
而对新四军来说,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。在艰难的敌后抗战中,每一次胜利都是宝贵的,它让战士们相信,只要战术得当,指挥有方,以少胜多并非不可能。
多年后,已经成为开国少将的彭明治在回忆录中写道:
“建阳之战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战争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对手,而是自己的恐惧和犹豫。当你觉得敌人强大的时候,敌人可能也觉得你强大。关键是谁能够保持冷静,做出正确的判断。”
“那个雨夜,当我听出敌人火力的虚实后,我知道机会来了。战争就是这样,危机中往往蕴含着转机,就看你能不能抓住。”
“我要感谢我的部队,感谢每一个战士。没有他们的英勇和服从,就没有这次胜利。特别是王东保同志,他的警觉救了我们所有人。”
王东保也活到了新中国成立,后来担任了某军分区政委。每当有人问起建阳之战,他总是说:“我就是运气好,碰巧撞上了鬼子。真正的英雄是彭旅长,是他的果断指挥,才有了最后的胜利。”
历史就是这样,由无数个偶然和必然组成。建阳之战看似偶然——如果王东保没有发现潜入的日军,如果彭明治没有听出敌人火力的虚实,如果部队没有立即执行反击命令,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
但这种偶然中又有必然。新四军长期的游击战经验,造就了他们高度的警惕性和灵活的战术;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他们顽强的意志;共同的信念让他们能够服从命令,协同作战。
这些必然因素,才是新四军能够在敌后坚持抗战,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。
建阳镇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城市。镇中心建了一座纪念馆,详细介绍了1941年那场激烈的战斗。每年的7月22日,都会有许多人来这里参观,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。
纪念馆里有一面墙,上面刻着在建阳之战中牺牲的87名新四军战士的名字。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,最小的只有16岁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,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,最后长眠在这片土地上。
墙的正中央,刻着一行字:“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,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。”
这也许就是对那个雨夜最好的注解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建阳之战只是一个小小的浪花,但正是这无数的浪花,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洪流。
每一个牺牲都有意义,每一次胜利都值得铭记。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《新四军第3师战史》,解放军出版社,1989年版彭明治:《征战岁月——一个新四军旅长的回忆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2年《盐城文史资料》第8辑,收录王东保口述史料,1995年《侵华日军江苏作战记录》,江苏省档案馆编,2005年陈毅:《关于新四军建设的几个问题》,载《新四军回忆史料》第二集
配资论坛是什么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